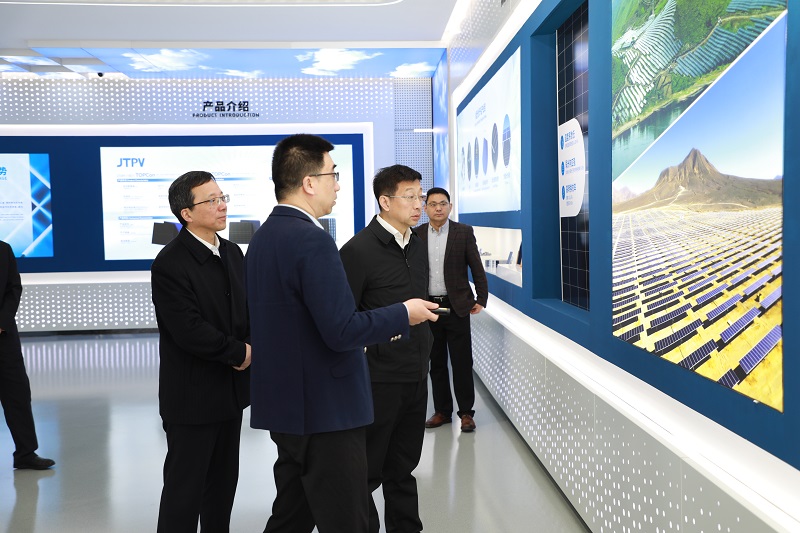——读小说《新纪元》有感
张珍
《新纪元》是碧荷馆主人于1908年连载在《小说林》上的一部未完成的政治小说,作者至今身份不明,只知他的另一部作品为《黄金世界》。《新纪元》的故事设定在西历世纪末的1999年。此时的新中国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政治上“久已改用立宪政体”、中央及地方各有议院、议会,而且“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人口一千兆,军队六百万”。中国的强盛引起了白种各国的猜疑和联手抵制,恰逢此时欧洲匈耶律(匈牙利)国境内匈奴后裔黄种人与欧裔白种人之间发生纠纷,酿成内乱,黄种匈王求助于中国大皇帝,中国随即出兵远征欧洲,挑战白种列强,最后迫使白种诸国签定城下之盟。英、俄两国拒绝签字,新的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这部小说既没有谴责小说那样对社会现实尖锐的讽刺,也没有狭邪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情感,叙说故事也是一叙到底,谈不上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情节,在艺术上似乎看不到什么闪光点,因而尽管有被翻印,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这在这部小说自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作者把目光投向世纪末——西历1999年(黄帝四千七百零六年),来展开他的政治狂想,虚构出一个理想的“中国”。其中种种匪夷所思的想象既反映了作者对未来世界的现代性探索与思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人们对清末社会现实以及战争的焦虑。在错综的时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人们极度的痛苦以及对未来的现代幻想。
一 政治小说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对‘现代’的认识,需要与一个权力过程联系起来一起考察。这个权力过程表现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民族国家的反抗,以及伴随这种关系而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痛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
在中国文学参与建构、确认民族国家,完成对于中国的想象、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小说这一文类表现尤为突出。小说与现代政治伦理思想相联系是中国古代小说所不具备的现代性特征之一。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兴起了文学革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中“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大力宣扬小说的政治功用,他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则必自新小说始。”当时报社、杂志社林立,争相发表小说,翻译小说、狭邪小说、公案小说、科幻小说等充斥市场,小说的商业性特征开始凸现,与传媒的结合也得到了完美的诠释。小说成了当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国家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路(《被压抑的现代性》)。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了《新小说》,并连载了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小说,其他类型的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影响。于是当时的小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宣扬政治教化,并吸收借鉴了外来文学的创作手法与素材,成为与中国传统说部不同的“新小说”。按照内容来划分,《新纪元》既可以被看作是科幻小说也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小说,然而从政治宣传的功用上来看,《新纪元》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小说。
在《新中国未来记》开创了中国政治小说的先河之后,时人有不少跟风之作,如《未来世界》、《未来教育记》、《世界末日记》、《新中国》等等,也包括本文重点叙述的《新纪元》。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它们的书名便可以看出来,即极力地畅想中国的未来,描绘几十甚至百年后中国的政治蓝图。文学作品除了可以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社会现实外,也可以幻想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这是创作者内心世界的外化,集中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想象。
当时的中国已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关于民族的想象已产生萌芽,新兴的政治小说中,民族国家意识甚至是种族意识得到了充分且外露的表达,小说作者在虚构未来世界的同时必少不了想象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进步志士对理想社会与社会革命的憧憬,也可以探讨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起源。
《新纪元》可以被看成是作者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与新中国摆脱欺凌、国富民强的强烈愿望的文学表达。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黄之盛”、“黄之强”、“扬国威”、“华日新”……这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名字寄托了作者强烈的愿望。而小说第三回中国大皇帝对元帅黄之盛说的话也颇有深意:“元帅此去立功数万里外,替黄种二千兆同胞争一口气,寡人敢为国民代表敬奉薄酒一杯,愿元帅此去早奏凯歌,归来同享太平之福。”“替黄种二千兆同胞争一口气”不止是小说中大皇帝的愿望,也是作者与同时代无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同胞的心愿。
小说中新中国已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政体,开设议会,国家富强、人口众多,中华民族已成为一个强大到令西方列强感到威胁的民族。然而,这种民族想象却打上了鲜明的种族主义的烙印。作者区别不同的民族采用的方法便是简单地将其划分为“白种”、“黄种”、“黑种”等,而中国则拥有“黄种”的宗主一样的地位,小说第三回标题为《救同种飞电起前勋重专征同僚设祖饯》,第十二回标题为《为黄族刘教习下山 遭绿气傅统领殉国》,都明确表现了“现代人”的民族意识与种族意识。世界上一切黄种民族皆为中华民族的隶属国家,以中国为尊,甚至被要求统一采用中国的“黄帝纪年”,而白种人则一直采用西历纪年,时间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可与政治发生关系,于是西方国家将中国在黄种民族中推行黄帝纪年看成是中国要联络黄种来与白种对抗的先声,并因此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直到机械钟测定时间的一致性与时间在社会组织中的一致性相适应以前,时间都一直是与空间(和地点)相联系的。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相一致,直到本世纪才得以完成。它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日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标准化。”(《现代性的后果》)作者选用“统一时间”作为战争的诱因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对现代的预见性的。
在作者的想象中,种族的力量甚至超越了民族的差异与冲突。在面临种族威胁时,同一种族内部不同民族的矛盾被有意无意地消除了,小说第一回白种各国列出的对付中国的办法中第一条便是“全球白种各国自此当结为一大团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黄种各国也是在中国的领导下积极地与白种对抗。在这里作者似乎过分强调了种族主义而忽略了现实中其实欺凌中国的并不只有白种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与日本的矛盾空前尖锐,而奇怪的是在《新纪元》中作者除了曾一笔带过日俄战争外,对日本只字未提,作者应当是把日本划进了黄种的圈中,把它默认为对抗白种的同胞了。这种想象与现实的不协调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作者并未意识到民族与种族的模糊区别。此外清朝人脑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的思想对作者也产生着影响,作者仿佛从内心深处拒绝面对那个曾经臣服于中国的弹丸小国如今竟然在中国的领土上大肆侵犯与掠夺。既然不愿意面对,那么就在小说中直接忽略掉了,这一段空白浸透着的是血与泪。
作者描绘了他对未来世界的民族国家想象,然而这种想象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并未建构出系统的国家理论,他所想象的新中国实际上是当时欧洲列强的翻版,而所谓种族之战也带有国家复仇主义的色彩。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愿望便在想象中得到充分发泄,而一个被欺负的人渴望成为的人物正是在现实中欺负他的人的形象,因此,作者构建的未来的理想国家只不过是当时已经存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具有太大的开创意义。在作品中,作者幻想着“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小说最后一回战胜的中国强迫白种各国签下的条约:
一 自黄帝四千七百零七年正月,即西历二千年三月起,各国俱承认中国有自保护匈耶律(匈牙利)之权。
二 各国此前所有派往匈耶律之水陆军队,俱于一月内撤退,并认偿还匈耶律兵费银五十兆两。
三 此后与中国同种之国均以黄帝纪元,其仅为黄种而非中国同种,有愿以黄帝纪元者,各国俱毋庸干涉。
四 各国当公认赔偿此次兵费银一千兆两,以五百兆归黄种各国,分作十年交清。
五 美、澳、非三洲内华人侨居之地方,俱画作华商租界,中国政府于各该租界内应有治外法权。
六 新加坡、锡兰岛、孟买、苏彝士河、阿德利亚基克海峡等处,俱许中国屯泊军舰,并许中国军舰有航行苏彝士河及地中海之权。
七 中国人准在欧、美两洲无论何国境内传中国之孔子教,各该国政府当力任保护之责。
八 美、澳两洲此次华民产业、商务损失之款,各国当另偿银五十兆两,并予以巴拿马河通行航业之权利。
九 合约签字之日,中国即将现在阿德利亚基克海峡之舰队撤回三分之一,馀候初次赔款交割后再行撤退。各助战国之兵舰亦照此办理。
十 合约签字之日,中国即将捕获之俘虏送还各国,各国当认还各项费用。
十一 此次合约告成之后,各国仍可派遣公使驻扎中国北京,中国亦可派遣公使驻扎各国,彼此重敦睦谊,与未战之前无异。
十二 此次合约用华、英两文缮写,计共两份,日后如有词义不甚明白之处,当以华文为凭。
这十二条和约俨然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拼凑组合。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共同的伤痛,贫苦的中国百姓为之承受了更重的负担。这虚拟的和约可以看做是作者郁积已久的悲痛的发泄,百年后的中国以胜利的姿态逼迫西方各国签下“城下之盟”,反映了人们对战争胜利的渴望。文学是社会性的活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心中郁结,从而诉诸笔端。一个与现实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在身份与时间的错位中寻找安慰,作者的这种政治想象背后所隐藏的挣扎与痛苦让人唏嘘不已。
二 落后与挨打中晚清进步志士的科技狂想
《新青年》大力倡导用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而这种思想在清末就已有发端。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逐渐完成,西方国家以及维新后的日本依靠新兴科技的力量日渐强大,并开始资本积累所必须的对外扩张,中国仍沉浸在“大国迷梦”中不可自拔。战争的失败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开始,到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维新派与改革派的政治体制之争,中国经历了一个学技术到学制度的变化过程。战争使当时的人们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中国的仁义礼智敌不过外国的坚船利炮,这使时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先进的科技。
在这种大背景的影响下,《新纪元》的作者似乎是一个科技狂热者,在他的想象中,百年后世界的科技发展到了极致,人们利用科技上天入海无所不能,“新时期”战争的胜负与科技的强弱直接挂钩。在小说的这样写道:
“现在世界上所有格致理化一切行下之学,新学界都唤作科学。世界越发进化,科学越发发达。泰西科学家说得好: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是汽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是电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是光学世界。照此看来,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那科学的发达,一定到了极点。”
“世界的进化与科学的发达,为同一比例。”
“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都学问的了。”
作者的这一番论述,显示了他对科学敏锐的认识与整体把握,也折射出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认识的一大进步:科学已不只是“夷”的“长技”了,科学与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中国不能忽略科技的作用。这种颇具现代气息的认识在《新纪元》中得到近乎夸张的呈现。
首先,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个个都精通科学技术,掌握着一种或几种“绝活”,俨然是科学家或技艺高超的技术工人。小说的主人公黄之盛是“州实业学堂里化学教习的儿子,于格致理化之学都有心得,在理科学堂卒业后,又在天文、农务、水师、陆师、万国语言等专门学堂一一就学,满腹经纶、浑身才干”;黄之盛的妻子“自幼即喜研究光学,狠造出几件新奇有益的器具”;当朝首相的侄女金小姐虽然年仅十四五岁,但也“于光学颇知一二”;黄之盛的师父刘教习更是一个隐居深山的方外高人。他们的对手也极其重视科技的作用,在征兵启事中明确声明:各国臣民有精于科学、发明新式战具者,准其携往战地,用以破敌。这场战争可以看成是属于不同种族的两方科学家在科技上的交锋。
其次,作者利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展开科技狂想,种种匪夷所思的发明器具在文中不断出现:
可以防止军舰触水雷爆炸的“行轮保险机”,使行驶方便的“海知觉器”、“海战探险器”,免去潜水雷艇掩袭之虞的“洞九渊”,改变战争“炮声震地、烟焰蔽天”现状的“无烟无声枪炮”。另有“升取器”、“潜水衣”、“火油衣”、“电射灯”、“日光镜”等器具。欧洲军队也是如此,他们有“绿气炮”、“水上步行器”、“远射炮”、“速射枪”、“避电衣”等。除了能直接用于战争的发明外,还有“能将药水化分泥土,提取各种养料,以备军中乏食之时可以无虞饥饿”的方法,“能造水、火二法,预备军中不时之需”的方法等等。
在作者看来,科技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券”,这无疑夸大了科技的作用,反映了作者对科技认识的局限。
然而,在对科技的崇拜中,作者明显表现出了信心的不足,先进的科技基本都是由外国制造,中国人只是继承和运用,如第七回宝镜“洞九渊”上的注云:“此镜系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意大利人卑那所发明最新之奇器也。”第八回升取器上的刻字:“右升取器一种,乃十九世纪之末意大利人卑那所发明……”第十回避电保险衣上的镂字写道:“此衣为前百年间俄国大书院教习阿的米甫所造……”这样的例子几乎每回都有。作者这中心态和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只是一味学习外来技术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如此崇拜西方科技的心态主导下,作者仍没有与传统划清界线:埃及的潜水艇由鳄鱼牵引;无线电通讯受阻时,传统的信鸽再次派上用场。这是多么奇诡的画面。此外,“以水生火”从而火烧敌舰的做法简直是《三国演义》中周瑜火烧赤壁的现代化翻版;住在海底的婆逻洲一带渔户与外界连接的一林大雄树又像极了《西游记》中妖怪躲避外界追捕而使用的障眼法;婆逻洲一带渔户的渔户与世隔绝,仿佛身处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而“世外桃源”这个意向本身就在许多传统小说中出现过。传统与未来交织,这幅不协调画面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虽然作者在对科技以及中国的未来努力地做出现代性的探索,但终究无法与传统割裂。
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科学的发达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那时候的世界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作者对未来科技做出的畅想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科技认识的变化,人们把对战争的胜利渴望盲目地寄托于科技的强大之上,这种远离现实、无稽之谈的表象下,隐藏的是深刻的社会危机,迂回地折射了晚清社会的现实。当时的人们对科技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战争军用等层面,科技到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人们似乎还无暇考虑,所以,书中出现的种种足以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的武器以及会打破生态平衡的发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不是那么突兀。其实不只是中国,当时世界上的依靠科技兴起的国家都在尽可能地利用科技,发掘科技的价值。那是一个近代科技刚刚开始迅猛发展、具有无限可能的时代,人们对科技的崇拜来源于自身的需要,尤其是迫切渴望摆脱落后局面或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的时候。意识到科技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并试图加以抑制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在深切地感受到科技的负面效果加给人们的不良影响后,人类渐渐实现了对科技的较为全面的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走向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所以,值得肯定的是,在对科技重要性的认识方面,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将目光洒向世界,向着现代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三 “开眼看世界”:理想与现实在时空上的延伸
随着侵略的加深,处在晚清社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忽略外来的影响,知识分子具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洞察力与感知力,眼光也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有了全球性的视野,形成自己对这个发生了巨大改变的世界的认知。从小说自身的角度来说,“新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外来小说尤其是西方和日本小说的元素。《新纪元》这种幻想未来的政治小说在外来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原型。虽然这种借鉴还不够成熟,但作者已经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寻求新变。其次,作者渐渐形成的全球性视野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作者对世界的认知水平上升到新的高度。小说第一回中作者对科学的总述便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较为整体的把握:“现在世界上所有格致理化一切形下之学,新学界都唤作科学。世界越发进化,科学越发发达。泰西科学家说得好: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是汽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是电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是光学世界。”在这种视野下,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新奇的事物与现象都成了作者所描写之物。
1、新女性。虽然康梁维新派在当时大力鼓吹妇女解放,然而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尤其在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对待妇女的观念还滞留在从前的阶段,认为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品。而在小说《新纪元》中则别是一番光景。虽然小说中有名有姓的女性只有两位——主角黄之盛的妻子金景媛和首相的侄女金凌霄,而且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但是作者笔下她们的形象已经突中国传统小说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二人精通科学,都是饱学之士,不仅如此,她们深明大义,有勇有谋。金凌霄一直随军作战,在危机时刻给黄之盛出谋划策;金景媛则从一开始就支持丈夫的“正义之战”,在中国军队遭遇危险时,不顾个人安危带着自己掌握的科学器具前去营救。
碧荷馆主人的这部小说一个致命的缺点便是人物符号化,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丰富的内心世界,所有人物的出现只是为叙述故事服务。这两个女性角色也不例外,她们似乎没有女性的感情,只是冰冷的符号,这也许可以归结为作者的写作水平。但从作者的叙述中已经看以看出他对女性的新的认识,女性不再只是男性的附庸,她们可以与男性并肩作战,一较高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突破。
2、报纸。自报纸在中国创办以来,便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印刷传媒可以上升到权力的高度,因为掌握了话语权便意味着在政治上增添了砝码,进步志士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不论是维新派还是改革派,都尝试着创办报纸以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政客们也常常关注着报纸上的新闻,揣摩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形势。报纸成为一种新兴的传媒,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即使是供人消遣的小说在报纸上的连载也脱离不了政治的气息。
《新纪元》的作者没有忽略这一点,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了这一社会变化。小说主人翁黄之盛闲居在家时依然关注的时事,在家乡创办了一份报纸来发表政论,“报馆里所出的报纸,每日总要行销数万张。因为报纸上的论说虽离不了急激党的宗旨,然持论极其正大,所以这报纸不但北数省的喜欢阅看,就是南边长江流域一带,也处处畅销。只为这报纸于政界上极有势力,所以急激党中的人都把黄之盛当作泰山、北斗般看待;就不是急激党中人,也都说黄之盛是当世的祥麟威凤,仰慕得不可名状。”
当时社会上报纸的力量是否有小说中的那么强大我们不得而知,但作者想象的是百年后的情形,相较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作者的推测还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3、海外移民。伴随着外来物品的倾入中国,中国也有大批移民向外流动。对中国而言,海外移民是一个较新的群体,少有文学作品涉及。碧荷馆主人则十分敏锐,他的另一部作品《黄金世界》便描写了中国在海外的移民的悲惨生活,并想象着这些移民推翻了当地政府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里又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国家与种族概念的模糊把握。《新纪元》中提及了这些海外移民,他们也在移民地推翻了当地政府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作为黄种国积极响应中国的战争号召。移民的华人成了统治者,并建立了国家,这又是作者的国族想象。
作者对当时世界的格局有着较为准确的了解,他的笔下出现了多个国家的名字,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洲、不同的民族。作者是否去过国外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已有了超越前人的眼界。
作者笔下的新鲜事物着实不少:因西方侦探小说引入而流行起来的“侦探”一词,在作者笔下便具有了军事间谍的意义;海战中忙着救济白种伤员的红十字会也时不时地出现;电报则是取代了以往的通讯工具,在军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铁路四通八达,人们出行乘火车甚至是坐气球……
看到这些不难发现其实这都是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的事物,作者一方面承认百年后世界上的科技一定是发展到了极点,另一方面他的思维却还是突破不了时间的限制——百年后的世界与当前并无太大改变,只不过中国已经变得和现在的西方一样了而已。晚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睁眼看这个世界,意识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这种全球性的视野是走向现代所必备的元素。可惜的是,作者只是将现实中较好的事物在时间上做了延伸,他在想象着未来,却摆脱不了列强的影子。
四 结语
限于自身的艺术价值,晚清的政治小说在兴盛了一段时间后便沉寂了,人们的审美趣味转向更加世俗的言情、狭邪之类的小说,如民初兴起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小说。梁启超期望的通过小说改善“群治”的初衷最终没有实现。但不能因此一笔抹杀政治小说的价值。《新纪元》等政治小说有意识地摆脱中国传统说部的框架与模式,从书名的“新”字便可看出一二。作者已经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出了晚清社会的种种变革,对清末现代化的转型有了深切的体会,他的不够成熟的全球性视野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当时国家实际上的现代化程度未必与作者的深切感受形成正比或对应的关系,作者畅想未来,描绘现代民族国家的蓝图,狂热地崇拜科技,他面对的是一个确定的过去和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他的种种关于现代性的想象也许会和时间、空间发展的真正轨迹相背离。同时,种种主观与客观条件的限制,又使这些想象无法挣脱现实的藩篱,所以,小说中不乏荒诞怪异的场景。然而,这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清末“新小说”的艺术价值普遍不高,但却以迂回的笔法折射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危机。《新纪元》的作者对未来的想象充满种族的激情,然而其想象模式却摆脱不了现实中国受凌于外国的阴影;作者面向未来,实质上却走回了过去。
这是一个悲情的想象,它浸透着处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边缘苦苦挣扎的中华民族的血与泪。这个民族是有梦想的,她也梦想着能够早日摆脱外来的欺凌、早日实现富强,开创一代盛世。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梦想的实现在当时却以幻想的形式在文人政客的笔下呈现。文学记录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衰落,以深情或冷漠的笔触去探寻不同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小说虽长期被视为“小道”,但在那个风起云涌、不断变革的时代,它也承担了这样的使命。“现代性”在作者的笔端流露,承载着现实的痛苦与梦想的重量。